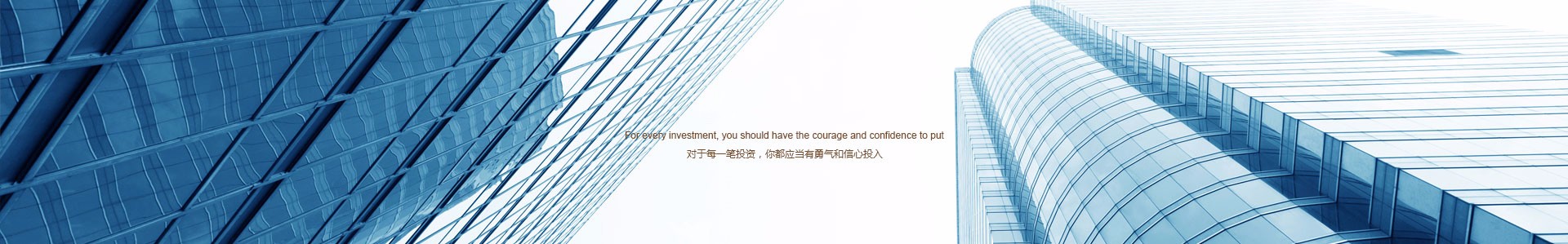“思·鉴”录|基金会负责人之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研究米兰体育- 米兰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
2025-11-03米兰体育官方网站,米兰体育平台网址,米兰体育官网链接,米兰体育app下载网址,米兰,米兰体育,米兰集团,米兰体育官网,米兰体育app,米兰体育网页版,米兰真人,米兰电子,米兰棋牌,米兰体育APP,米兰体育下载,米兰体育APP下载,米兰百家乐,米兰体育注册,米兰体育平台,米兰体育登录,米兰体育靠谱吗,米兰平台,米兰比賽,米兰买球

根据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①,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根据2024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基础术语》,社会组织是指在各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②;根据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③,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为目的,按照该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关于三者的关系,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④,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会团体、基金会均系社会组织下同一等级的子概念。
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社会组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此之后,众多新修订的法律规范出现了将规定中的“社会团体”替换为“社会组织”的情形。如1989年出台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第二条将基金会囊括在社会团体中,但1998年出台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则删掉了这部分,同时制定了之前没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概念。除此之外,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中,2015年至2019年度均使用“公益性社会团体”这一概念,2020年起也变更为“公益性社会组织”⑤。上述法律规范中用语的变化体现了近三十年“社会团体”含义的转变,1998年以前“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尚未出现,依据当时出台的法律法规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团体”与如今“社会组织”涵盖范围相同,直至1998年“社会组织”概念出现,明确基金会、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共同组成社会组织,自此之后新修订的法律规范逐步完成了用词的替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发布时间为1997年,从立法本意出发,应当更加宽泛地认定该条文中的“社会团体”包含基金会、狭义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该如何理解“委派”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委派”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委派主体特定。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委派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0年《意见》)对委托主体进行扩大解释,增加了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⑥,但根据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3年《纪要》),对于被委派者的身份却无过多要求,被委派者不限于委派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除此之外,为保证委派的合法性,委派主体应具有委派权,且不得违反法律规定。2.具备实质委派性质。一方面,委派主体与被委派者之间存在事实意义上的委派行为与意识。对此,《职务犯罪检察业务》中载明委派可以是事前、事中的提名、推荐、指派、任命,也可以是事后的认可、同意、批准等,但不包括单纯的事后备案行为,同时结合2003年《纪要》的解读及2010年《意见》可知,委派形式多种多样,且可以发生在事前、事中或事后,不论书面文件形式或口头形式,不受任命机构与程序的影响,但需确有证据证明委派主体与被委派者之间具有明确的委派与接受委派的意思表示,如事后双方的行为⑦等,单纯的事后备案行为等不具有实质委派性质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委派;另一方面,被委派者需经历具体或抽象的位置变化。“委派”一词的文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二款中“到”字的表述,均可体现被委派者接受委派后,应当产生地点或处境的变化⑧,或是到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是在同一单位的不同职位从事委派者交付的工作。3.被委派者与委派主体之间具有行政隶属关系⑨。即被委派者不仅应作为委派单位的代表在被委派单位从事公务,还需接受委派主体的领导、管理和监督,无论原本是否为委派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4.被委派者从事的应系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该条件的含义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具体论述。
回归对基金会负责人身份的探讨。基金会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其登记管理机关为国务院民政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最终审批登记、年度检查及日常监督管理等工作,其业务主管单位则因基金会宗旨与职责的不同而不同,由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担任,主要负责指导、监督基金会依照法律和章程开展公益活动等工作,判断基金会负责人是否具备“委派”要件,应厘清业务主管单位与基金会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由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若被授权组织不满足刑法及2010年《意见》规定委派主体中的任何一种,那么该基金会负责人不具备认定“委派”的前提条件;若满足条件或者由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应先通过查阅基金会章程或历次理事会换届材料,进一步考察业务主管单位在基金会负责人任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事前提名、推荐,事中指派、任命或事后追认、同意,还是仅仅进行形式审核或单纯备案,如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章程规定理事会换届改选时由业务主管单位参与提名候选人并组成换届领导小组,理事的增补也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因此该基金会项目合作部主任王魁嵩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最后,还需考察业务主管单位是否发挥领导、监督、管理作用,切实监督、管理基金会负责人依据法律及章程组织、领导基金会开展公益活动。只有同时满足委派的四个条件,在判断基金会负责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时才能认定其符合委派要件。
1.国家意志性,即代表国家或为了国家利益从事公务。(1)国家代表性来源于法定委派主体的委派。具体可从以下3点进行判断:首先,在基金会中,只有基金会负责人以及理事、监事才可能具有代表国家指导、监督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的权力外观⑪;其次,以国家、政府之名从事相应公务必须具有相应的权限,该权限来源于法定委派主体的委派;最后,只有被委派的基金会负责人代表国家利益指导、监督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时才具备国家代表性的实质内核⑫。(2)区分公共事务与国家事务。2003年《纪要》将从事公务行为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和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1条第三项及《公益事业捐赠法》第7条,基金会在社会募集的善款属于公共财产而非国有财产,因此判断基金会负责人是否从事公务,应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第一种类型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在刑事法律领域,公务应限缩为国家事务,应对广义的公共事务与国家事务进行区分。一方面,国家事务是公共事务的下位概念,且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释义》(以下简称《释义》),公共事务分为国家事务和集体事务,其中国家事务的实施目的是实现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国家职能,集体事务则限于集体组织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处理国家事务的权限来源于国家,行为人必须代表国家进行相应活动,而公共事务无此限制 ⑬。
2.公共管理性,即公务是一种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活动⑭。2003年《纪要》及《释义》明确规定公务需为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一般不认定为公务,在司法实务层面,管理性也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必备条件,通常认为劳务因不具有管理性而不属于公务,笔者同意该种观点,因为不具有管理性的单纯劳务行为不涉及国家与民众的信赖关系,不在职务犯罪的保护法益之内,但“公务与劳务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售票员从事的虽为劳务工作,但实际上也兼顾管理车费等公共财产的工作⑮。那么该如何区分刑法上的公务与劳务行为呢?除了工种外,还可以结合行为人具体承担的岗位职责及具体罪名对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要求进行具体分析,若行为人具有并利用了自己管理、监督国有财产或组织、管理某一国家事务的职务或便利条件,那么该行为人就应认定为从事公务而可能涉嫌职务犯罪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立法上的兜底条款,在认定时应从严把握。横向对比其他法律规定,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列举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该种情形 ⑰,2003年《纪要》详细规定了该种情形包含的具体类型,2025年《监察法实施条例》同样明确指出该种情形的范围,可以发现在我国“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均有直接、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 ⑱。最高法熊选国、苗有水对谈中载明,“所谓‘依据法律’,是指他们从事公务活动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这可以体现为法律直接加以规定,也可以由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管理职权以及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 ⑲。”而《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七条是对于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的规定,并非直接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负责人可依据该法律条文从事公务活动或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依据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不能仅依据该规定认为基金会负责人在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若依据该规定作为判断依据,则基金会负责人仅需符合从事公务要件即具有主体身份,可能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不当扩大。
深入探讨基金会负责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绝非纯粹的学理思辨,而是关涉慈善公信力重塑、社会资源分配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现实命题。明确其法律身份,是精准适用法律规范、强化司法震慑的前提,是堵塞监管漏洞、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的制度基石,更是回应社会关切、重建公众对公益事业信任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探索基金会负责人身份认定的合法合理路径,但实务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因基金会数量较多,业务主管单位可能难以按照章程规定与基金会负责人形成事实意义上的委派及行政隶属关系,在该种情形下应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又如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负责人在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要求的前提下,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法律规制,为更好构建有效遏制腐败的监督机制,仍需要对现存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⑤《关于2015年度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16年第155号, 2016年12月14日发布;《关于2017年度第二批和2018年度第一批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19年第69号,2019年5月21日发布;《关于2019年度和2018年度第二批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20年第31号,2020年6月4日发布;《关于2020年度——2022年度第二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21年第5号,2021年2月20日发布。